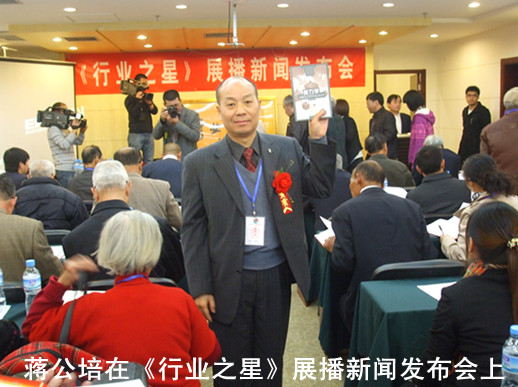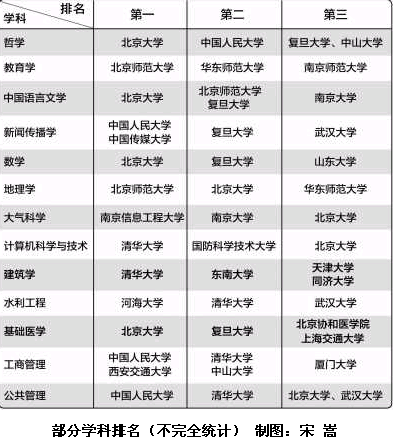从30名院士联名“反对”,看科学之短长
光明网评论员:昨天(4月10日),《中国科学报》刊登了30位院士联名反对“中式卷烟”入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消息。这个“反对”,起因于科技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在3月22日发布的第67号公告。在该公告公示的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受理项目目录中,“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是候选项目之一。30位院士反对把这个项目列入受理项目目录,要求有关部门“严肃面对公众期待及国家形象”。
这个“反对”,实际上是一些院士继去年底反对长期从事烟草化学研究的人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之后,再次亮明其对烟草业发展的态度。这其中,既有科学之争,也有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比如,“减害降焦”的院士入选业绩,其所受到的质疑,就是所谓“减害”,在半个多世纪前就为众多国外学者所否定,以此为业的院士却并没有拿出任何实验材料推翻否定的结论,也没有任何指标说明“减害”的效果。又比如,所谓的“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的内容,其目的是推动更多的人吸烟,而这恰与国家科技进步奖的最终目的相悖。
表明“反对”态度的院士,其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国家促进科学发展的目的,在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而烟草行业发展的目的却正与之相反。烟草业虽然是国家的纳税大户,成为国家汲税的重要来源,但是国家从烟草税收中所得,远不足以支付由吸烟造成疾病的医疗费用支出。
从上述争议中,人们可以看到,有关烟草业的“科研成果”能否入选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受理项目目录,从事烟草科学研究的人能否当选有荣誉称号性质的院士,其争议所涉及的范围,其实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畴。这个争议所引申出的问题,尤其值得以“科学发展”为圭臬的人们深思再三。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科学应用有无道德限制?科学性是否天然具有正当性?这些看似抽象的问题,实际上正规定着人们对现实发展路径的选择,并由此深刻地影响着人们日常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系统的科学及其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及其知识,从概念到理论,主要来自西方。西方的科学被引入中国,天然地挟带有“船坚炮利”的功利主义考虑。“科学救国”的口号,在理想化了科学功用的同时,也为科学蒙上了一层道德的亮彩。在科学之途上,长期步西人后尘的历史,让艳羡“船坚炮利”的人们,对科学始终带有一种膜拜的心理,唯恐学习不周,唯恐落于人后,由此,哪里还敢对科学本身有所反思,有所怀疑,甚至有所反对。
在西方,科学是在与宗教相辅相成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面对着人本主义对其的反思和制约。“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种现象,即使在科学繁荣景象如今日之目不暇接的情况下,也仍然如此。科学越发展,“揭露”出的人类无知领域就越多。因此,科学的“已知”固然值得欣慰,但绝不能由此张狂;而科学的“无知”虽不值得恐惧,但却不应使人失却敬畏。
在科学思维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素质的情况下,人格中道德“因子”的重要性不是下降了,而是空前地增加了。
因此,在当代,人们想事情,干事业,当然要看在科学上可行不可行,但是,也同样要看在道德上允许不允许。以为科学上的可行之事,便可无顾忌地“大干快上”,结出的将是“科学之恶果”。
(资料来源“光明网”,作者“光明网评论员”)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