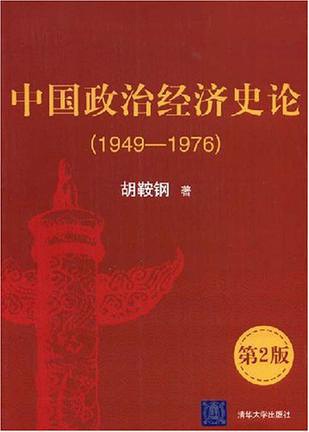寻找失落的英雄
寻找失落的英雄
这是一段用鲜血和泪水写下的历史,又是一段隐没的历史。六十多年前,在
抗日的烽烟中,中国远征军被派往缅甸作战。战后,许多老兵在异国他乡经历了
痛苦的人生。他们的状况如何?他们对祖国怀着怎样的感情?曾以报道山西娄烦
尖山铁矿特大事故而为全国瞩目的记者孙春龙,将带您走进这些老兵的艰难岁月
寻找失落的英雄
——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国寻亲记
作者:孙春龙
1.在国殇墓园里,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
多年来,每每想起那个偶遇的老人,我的愧疚就会油然而生。一切都是因为
我的浅薄,当他激动万分地向我讲起那段历史时,我却始终无动于衷而又茫然地
看着他,我的迟疑与平静让他的激情陡然不再。
沉默,或许是一种更为绝望而又震撼的表达方式。
那是2005年6月中旬的一天,国际禁毒日前夕,我在缅甸北部采访当地的一
支民族地方武装宣布禁种罂粟一事,在宾馆的院子里散步时,看到一位穿着龙基
(缅甸男人穿的裙子)的老人正躺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你是中国来的记者吧?”就在我走过老人的身旁时,他睁开了眼睛,主动
向我打招呼。
我很诧异地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是记者?”
“谁来了这里,我都知道。”老人很得意地说,随后又解释说,“这个酒店
的老板是我的亲戚,我平时就住在这里,来来往往的人都知道。”说着,老人喊
宾馆的保安拿来一个小凳子让我坐下。
“你了解‘金三角’吗?”老人反问我。我说来之前看过不少资料。
“不要相信外界报道的那些,你要自己去调查了解。”老人对我说,“有好
多记者,走马观花地来一趟,加上一些渲染,回去之后就写报道,这是极不负责
任的。正是这样的报道,让‘金三角’越来越被妖魔化。”
老人的告诫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在谈话中得知,老人是国民党的一位老兵
,解放战争后败退到“金三角”,也见证和经历了“金三角”最为鼎盛和混乱的
日子。一生中最让他感到哭笑不得的一件事情是,他所在的部队退到“金三角”
后,曾经和这支地方武装的头目所带领的部队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战斗,但现在,
他和这个头目成了亲家。
“我们现在经常会聊起当年是如何攻打对方的。”老人笑着说。
但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对他的身份的追问会让他那般敏感。老人猛地
坐直了身子,指着我的鼻子异常愤怒地说,“你说,你们说我们不抗日,说我们
是卖国贼,那么你说,在国殇墓园里,我们那么多兄弟是怎么死的?”
老人的指责让我一时无所适从。我努力回忆着我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但脑子
里一片空白,我甚至连国殇墓园是怎么一回事也一无所知。
真正抵达国殇墓园已经是在两年多之后。
就在当初的那份好奇已经随着时间而淡定的时候,云南普洱德福经贸有限公
司董事长高飞打来电话,邀请我去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参加当地的克钦族每年一度
的狂欢节———目瑙纵歌,而出境就在云南腾冲的猴桥口岸。高飞是我非常要好
的一位朋友,做着木材、玉石、茶叶等生意,经常出入缅甸,由此也练就了一口
流利的缅语。
因为途经腾冲,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次邀请。从昆明坐飞机到保山,然后
再转坐汽车,抵达腾冲时已是深夜。入住兴华大酒店后,我就急切地向酒店总经
理鲁兴华打探国殇墓园的位置。让我激动不已的是,墓园就在离酒店百十米远的
地方。
谈到国殇墓园,鲁兴华同样是兴致勃勃。当我后来接触更多的腾冲人,不管
是官或民或商,我发现,他们对国殇墓园的感情,以及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是那
么一致地强烈和清晰。所以在两年之后,当我组织的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
回国寻亲时,他们力邀老兵们去腾冲,他们给予的欢迎之隆重,以及对于老兵关
爱之真诚,让我感动不已,也在预料之中。
而国殇,不仅仅是腾冲的国殇,更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国殇。
从兴华大酒店的窗户眺望,国殇墓园的方向,一片漆黑。那是一个很难入睡
的晚上,我一直在想,在即将到来的清晨,我该以怎样的一种姿势,走过这百十
米的路程,走进那段历史。
这里并不是一个游客必至之地。2008年1月7日早晨,当我顺着松柏掩映的石
板路拾级而上,绕过忠烈祠,抵达墓地的时候,那种久违的震撼和激动还是如排
山倒海般袭来。
整个山坡上,竖满了密密麻麻的墓碑,清澈的阳光透过高耸的松树,落在小
小的墓碑之上。青苔遍布的墓碑按建制整齐地排列着,碑文简单到只有军衔和姓
名。
是何等惨烈的战争,让这么多的生灵不在?是什么样的纠结,阻断了我们对
这段历史的传承?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以6个师的兵力强渡怒江天险,向侵占
滇西战略要塞腾冲达两年之久的日军发起全面攻击。腾冲攻城战役历时42天,第
二十集团军,以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结束了这场被日军称为的玉碎之战。
腾冲收复后,当地老百姓最先想到的,就是为战死的官兵修一块墓地,40多
万元的捐款很快筹齐,几个大户人家也无偿地将风水宝地———小团山捐献出来
作为烈士的安息之地。
2.历史认知上的代沟,已经难以用三言两语所能消弭
2008年4月初,我再一次抵达腾冲。这一次,是以一位记者的身份。从云南
腾冲的猴桥口岸边防检查站出境,穿过缅甸一个地方民族武装组织的区域,再经
过一段笔直的两边全是稻田的公路,而后经过一个架在伊洛瓦底江上由缅军守卫
的铁桥,就到了密支那市区。
这条仅仅三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祖国边境的公路,让许多人,用了一生也未
能跨越。
不过,对于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来说,他是幸运的。在整整离家70年之后
,他终于从这里回到了祖国,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乡。
见到李锡全,是在2008年4月6日的清晨。这个已经入赘异国的老人,最终因
为一场跨越国界、跨越党派、跨越一个甲子的回家之路,被列入2008感动中国候
选人。
找到老兵李锡全,是在老华侨董宝印的带领下。董宝印在密支那街头开了一
个杂物店,店门口摆着一个公用电话。我在使用他的公用电话时,他听到我在找
老兵,说他认识好几个,随后毫不犹豫地叫来他的孙女照看店面,主动要为我做
向导。他的孙女似乎很不情愿,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爷孙之间对这段历史在认
知上的代沟,已经难以用三言两语所能消弭。
祖籍云南腾冲的董宝印在1946年随同父母逃到密支那,从此落地生根。他的
五个孩子都已经参加工作,其中四个在台湾。
董宝印告诉我,在他小的时候,还曾在学校的组织下去位于密支那三英里的
中国远征军墓地扫墓,但现在,年轻人都不关注这些事情了,墓地也找不到了。
李锡全的家位于密支那郊区的华侨新村,这里曾是中国远征军的驻军所在地
,至今还留有几间二战时的铁皮房子。而在解放后,这里又成为难民营地,最终
成为一个华人的聚集区。
华侨董宝印带着我,穿过一个菜市场,拐过几道弯之后,来到了李锡全的家
。房子是木结构的,外墙用竹条编织,颜色已经发黑,外观已足以显示其家境的
贫寒。
至今,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董宝印向李锡全介绍了我的来意之后,李锡全
脸上流露出来的难以掩饰的激动。
李锡全的老家在湖南省桃源县,兄弟6个,他最小。抗战全面爆发那年,17
岁的李锡全和四哥、五哥一起从军,辗转广东、广西、云南多地。1943年,李锡
全所在的部队编入中国远征军第54军,随后展开了收复腾冲的战役。
李锡全是直属军部的辎重团的特务长,专门负责运送战场给养。1944年5月
11日凌晨,中国远征军打响了滇西反攻战的序幕。当日,李锡全所在的部队强渡
怒江,并随后从北斋公房翻越高黎贡山,挺进腾冲城。
在腾冲收复战时,李锡全右腿负伤。战争结束后,李锡全来到缅甸密支那的
英军医院治病,未随大部队开拔。内战爆发后,李锡全所在的54军被调到东北战
场,并最终在辽沈战役全军覆没。
在战争期间,李锡全曾和一同在云南当兵的两个哥哥联系过,但之后就没有
了联系。他也曾给湖南老家的父母写过信,但此时老家已被日本人占领,他并没
有收到回信。
在治好腿部的伤之后,李锡全留在密支那摆地摊谋生,并改名李云。几年后
他娶了当地的一位傣族姑娘做老婆,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姑娘。李锡全的孙女李
冬芬1986年出生,2005年从密支那大学毕业,虽然学的是历史,但她对爷爷在战
场上出生入死的经历一无所知,这位面相已经完全缅化的姑娘,唯有这个中国名
字和她爷爷的祖国有着关系。
后来我接触了多个生活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的第三代,他们和李冬芬一
样,对爷爷们所经历的那段历史异常陌生,那场为了民族存亡而进行的战争,对
他们来说似乎非常遥远。
在我采访李锡全得知他70年来没有回过老家,而且和亲人没有一丝联系的时
候,我突然问他:你想回家吗?出乎我预料的是,李锡全摇了摇头淡然地说:不
想。他有些自嘲地对我说:要两三百万元(缅币,100万缅币约合6500元人民币
)才回得到,我也老了,回不得了。
就在那时,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我告诉李锡全,我回国之后帮你找家
。我从采访本上撕下一张纸,让李锡全写下了他所能回忆起来的和家乡有关的所
有信息:湖南省桃源县白洋河鹅道咀,父亲李尧臣,大哥李松柏(又名李锡铃)
,五哥李锡番。
3.对这段历史的救赎不应该止于探索真相和细节的报道
密支那的老兵杨子臣经济条件较好,所以好多和老兵有关的事情,都由他出
面奔走。在众多华侨以及中国驻外机构的帮助下,杨子臣等老兵联名向缅甸政府
提出的在密支那重修中国远征军纪念碑的申请,终于在2009年初获得了批准。为
了这一批复,他们奔波了十多年时间。但因为经费问题,这项工作依然进展缓慢。
为当年的战友建一座纪念碑,是杨子臣此生最后的心愿。筹划这项事情的时
候,留在密支那的老兵还有100多名,但在我2008年4月到密支那采访的时候,这
里只剩下四名老兵。
在缅甸境内,其实还有两座未遭损毁的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其中一座位于缅
甸北部的果敢地区,另一座纪念碑在缅甸同古。1942年3月20日,中国远征军第
200师在师长戴安澜的率领下,与侵缅日军第55师团两个联队在同古城外发生激
战,第200师在此次战斗中伤亡2343人。
1951年,同古的华侨杨光汉等人筹资,在当时的中华学校校园内建立了一座
中国远征军纪念碑。但后来由于学校被缅甸政府收归国有,给祭祀带来诸多不便
。此情此景让生活在此的老兵杨伯方忧心忡忡,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华
人会馆的财神庙旁边,将原来的纪念碑迁出重建。
二战史研究专家戈叔亚曾一一考察过这些纪念碑,但当他在仰光郊区一个叫
做Taukkyan的地方,看到了一座气势宏伟、面积颇大的英国阵亡将士公墓时,突
然黯然神伤。那座公墓有6374座墓穴,墙壁上镌刻着27000多名在缅甸战役阵亡
的英军士兵的名字,其中相当部分是印度、非洲、缅甸籍军人,整个墓地有专人
管理。
而守卫同古纪念碑的,只有年迈的老兵杨伯方。
2009年3月,就在我抵达缅甸准备迎接这些老兵回家时得知,仅仅两个月前
的1月2日,这位在同古孤守数千亡灵的老兵与世长辞,终年89岁。他最终依然没
能逃脱客死异乡的命运。
在采访完密支那的老兵回国后,我在供职的《望东方周刊》上发表了第一篇
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文章《腾冲远征》,由一条路及人,及历史。
文章发表后,引起网友极大关注。趁此机会,我将李锡全找家的信息整理出
来,于5月8日发表在博客上。
5月9日下午,我突然接到湖南网友“桃源热线”打来的电话,说他基本可以
确认李锡全的家在桃源县青林乡。当日下午3时许,他们便联系到了李锡全的侄子
李谷伯。当天晚上,李谷伯给我打来电话,从一口浓重的湖南话中,我还是听出
了他的激动。一场战争,让这个家庭四分五裂。李谷伯说,他的父辈兄弟6个,其
中后面3个兄弟都去当了兵。其中四叔死在了新疆;五叔则在抗战结束后在云南安
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和家里有过联系;唯独六叔李锡全一直没有消息。
放下李谷伯的电话,我立即打电话给缅甸密支那的华侨董宝印,因为李锡全
家里没有电话,我让董宝印向他转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那一夜,我始终难以入眠。
5月10日一大早,我迫不及待地再次拨通了华侨董宝印的电话,让我意想不
到的是,董宝印在电话里告诉我,李锡全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痛哭不止,没有我想
象中的兴奋,反倒是更加痛彻心脾。董宝印或许更能体会症结所在,“他都老成
那样子了,他哪敢再去想回家的事啊,年轻的时候想回去,但找不到,也不敢回
,现在年老了,没有体力了,更没有钱,不去想这事了,死心了,家却找到了,
你说他能不伤心吗?”
作为一名中国的年轻记者,对这段历史的救赎不应该止于探索真相和细节的
报道,更应该积极参与到具体的事件之中。在没有任何思索和筹划的情况下,我
坚定地告诉董宝印,让他转告李锡全,我来帮他回家。
随即,我就向云南腾冲一家国际旅行社的朋友了解李锡全入境的相关手续办
理问题,并着手经费的筹集等一些准备工作。
5月12日下午两点28分零4秒,让我们失去8万多名同胞的汶川地震发生了。
事发一小时后,我在西安的大街上接到赶赴地震灾区采访的命令。
我清楚地记得在5月15日的傍晚,我正在安置灾民的绵阳市九洲体育馆采访
时,手机响了,传来一个颤抖而又急切的声音,“祖国发生地震了,我还回得了
家吗?”
在我的面前,是数万名失去家园或者失去亲人的灾民,他们脸上是让人心碎
的茫然。我毫不犹豫地告诉那位老人:我一定要接你回家,一定!
4.每个人的童年,一生都难以撇弃
6月中旬,在灾区采访一个多月后,我回到了家里。云南腾冲旅行社的朋友
告诉我,要接李锡全老人回家,存在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个是目前缅北正是雨
季,腾密公路几乎每天都发生山体滑坡而阻断交通的事,非常危险;更难的是,
李锡全老人没有护照,只能在云南腾冲县公安局办理外国人出入境证,而这个证
件,最远只能到达昆明,如果想出云南省,必须经云南省公安厅特别批准。
每一个问题都很棘手。而且回家的大约3万元资金还没有着落。我四处给人
打电话,动员他们赞助,每天都说得口干舌燥。有三位企业老板本来答应赞助此
事,但到第二天又都反悔。在这期间,我又接触了几位企业界的朋友,但都没有
了下文。
回想起来,这个活动在前期之所以费了这么多周折,是因为在当时这段历史
还是鲜为人知。而后来我策划的更大规模的老兵回家活动,并没有遇到太多的阻
力。2009年初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热播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段历史。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湖南一家上市公司F公司的董事长愿意倾力相助。我
立马飞往长沙。见到F公司的董事长之后,他竟然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了中国远征
军的历史。关于此项活动的意义,他甚至给出了比我更高的评价。原打算他赞助5
万元,他却愿意出20万。董事长考虑得非常周全,要求下属将李锡全回家后的被
褥也要购置齐备。同时提出为了把事情安排妥善,让我和公司的两名相关人员再
去一次缅甸,进一步核实李锡全的相关情况。
9月4日,我和F公司的两位主管来到密支那。
当天晚上,我们找到李锡全家的时候,他没有在。给我们带路的华侨董宝印
说,肯定是去邻居家看电视了。果不其然,没几分钟,李锡全回来时,一问,果
真是到邻居家去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李锡全家也有一台小的黑白电视
,但之所以去邻居家,是因为邻居家有卫星接收器,“可以看到中国的电视。”
李锡全并没有认出我,但他一见我们的面,就打问孙记者是哪位。得知是我
时,他伸出两只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满脸笑容。
F公司的一位主管就是湖南桃源人,他用桃源话和李锡全交流,李锡全答得
自如。让这位主管感叹的是,李锡全的家乡话说得还非常地道。
家乡,无非是一句方言,或者一个味道,抑或是一段记忆。
在李锡全的记忆里,他老家的村子旁边还有一个小池塘,他小的时候常去游
泳,或者抓了鱼虾回家吃。在李锡全回到家乡后,有记者陪他来到村子旁边,虽
然小池塘已经不在了,但他依然能说出当年的位置。
李锡全对记忆的维系来自一本中国地图册,这本地图册是上个世纪80年代买
于密支那,装订已经开胶,页码散开,但码放得依然很整齐。见到我们,李锡全
拿出这本地图册,一页页地翻开,在湖南那一页,他突然停下来说:“我的家就
在这里,想家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看。”
那一页是被翻得最烂的一页。这些色彩斑斓的小方块,对李锡全而言,就是
祖国和家乡。李锡全回到家乡后,这本随身携带的地图册让许多人泪流满面。
在缅甸曼德勒有一位老兵叫张富鳞,他的老家在山东济南,他对家乡的记忆
是一种叫作甜沫的食品,每次谈到老家,张富鳞都会说到甜沫,并感叹,“70多
年没吃过了,从当年离开家后就没吃过了,真想啊,那滋味……”说着还咂了咂
嘴,沉浸在回忆中。
5.明白告诉自己的官兵,国家从来没有也不会忘记和抛弃你们
F公司的两位主管对李锡全的情况了解之后,认为这次活动成功在握,他们
明确告知,等回去向董事长汇报后,最多一个星期,就接他回家。
意外的是,再次见到董事长,他已经不像上次那样爽快。原来他们北京的公
司总部领导对此事的批示并不明确。
就在为李锡全的事情焦虑不已的时候,另一个事情让我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2008年8月,我报道了山西省娄烦县的尖山铁矿瞒报安全事故死亡人数的事情,
因为上网的稿件很快被删掉,我又于9月14日中秋节那天写了一封《致山西省代
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贴在博客上,这封举报信后来得到温家宝总理批示而使
娄烦事件逆转,也正是这封信得罪了诸多的利益集团,让我不得不放弃去接李锡
全老人回家,转而开始半个多月的逃亡。
就在这封举报信让我焦头烂额的时候,此前曾多次参与报道李锡全回家一事
的《潇湘晨报》新闻部主任常乐联系我说,他们可以派记者去接李锡全回家,而
且经费不成问题。那时我已自身难保,就将此事托付给常乐。
后来我得知,《潇湘晨报》以及常乐的同行为此事亦费了不少周折。
10月19日下午5时45分,李锡全乘坐的K472次火车终于驶入长沙火车站,虽
然火车晚点4个多小时,但长沙火车站广场上仍然聚集着数百名对英雄怀着敬意的
人们。
好多细节不是刻意安排的,就像当李锡全走出火车站时,欢迎的人们突然唱
起《义勇军进行曲》一样;就像曾参加国际维和部队的国防科技大学英语教员李
洪乾,当得知李锡全回家的消息后,专程前往慰问,并向他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一样。
后来当我看到美国影片《护送钱斯》时,更加体会到尊重的价值。《护送钱
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钱斯·费尔普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下士,在伊拉
克战场上牺牲。影片展现的是他的灵柩在穿越大半个美国时,在遗体运输、遗物
整理、入土下葬等多个环节上,各路人士给予的礼遇。
“ 明白告诉自己的官兵,国家从来没有也不会忘记和抛弃你们。”这是影片
中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台词。
即使在今天,美国依然不惜成本地在寻找当年在朝鲜战场或者越南战场牺牲
的官兵的遗骸,并想尽千方百计将他们带回祖国安葬。
命运中总会有很多的巧合。
10月19日,当李锡全结束70年的远征终于回到湖南时,我也结束了半个多月
逃亡,回到西安的家中。因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我的举报信的批示以及国务院
相关部门的积极调查认定,我的报道和举报得到了官方正面的肯定。一时间,中
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多家媒体均对我进行了报道,朋友笑称我也从狗熊变成了
英雄。
那一年年末,我和李锡全同时进入2008感动中国候选人。
李锡全从云南入境是在10月12日,摄影师为我们留下了激动人心的瞬间:李
锡全颤巍巍地走过冰冷的中缅边境四号界碑,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位清瘦的老人
,泪流满面。
在回到青林乡的第二天,李锡全就来到父母的坟前。那一天,天空飘着小雨
,李锡全在父母的坟前长跪不起。当年,母亲送他出征的一幕至今还深深地记在
李锡全的脑海里。
“母亲,我回来了,回来晚了。”在母亲的坟前,李锡全喃喃自语。
在抗战史上,湘军的地位举足轻重。8年抗战,约210万名湖南人投身疆场,
他们的身后,也是210万名整日牵挂孩子归来的母亲。又有多少,最终未能骨肉
相见?
毫无疑问,李锡全的回家是一次每天都浸泡在泪水中的旅程。从听到找到家
乡亲人的消息,到跨进国境那一刻,到在国殇墓园里和当年的战友交流,再到面
对长沙火车站数百名市民的热烈欢迎,以及见到和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还有跪
倒在父母的坟前。而更伤心的,则是又一次离别。他又回到了缅甸。那一天,他
再次来到父母的坟前,含着眼泪对父母说:“我这几天要回去了,我以后回来再
看你们。我家里那边还有人,本来我也不想回去了。”
以后,对于这位90岁的老人,还有多少以后呢?
6.如果更早的时候我就组织了老兵回国寻亲,那该是一支多么壮观的队伍啊
在云南腾冲采访的时候,曾遇到过正在拍摄电视连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
的一些工作人员,以及正在采访中国远征军老兵制作口述历史节目的央视著名主
持人崔永元的团队。在和这些同龄人交流的过程中,我也切身感受到了他们对于
这段历史所表现出的投入和内心的挣扎。
崔永元开始关注这段历史是在2002年,机缘是在此之前去日本的一次访问。
那次去日本,崔永元在NHK(日本广播协会)参观时被他们的一个影像库所吸引
。NHK有一个特别行动组,专门作一些纪实性的采访,但不管播不播,NHK每年都
会给拨很多钱。在这个影像库里,崔永元竟然发现了张学良在“九·一八”之后
一段长达30分钟的演讲实录。这段演讲中,张学良说,委员长说了,两年之内,
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在这个影像库里,关于中国的资料密密麻麻。
崔永元大受刺激。回国后,崔永元找到台长,说中央电视台每年应该拿出一
个亿或者几千万元专门作历史资料的收集,从公益讲也有用,长远讲是给子孙后
代留下。后来台长拍着崔永元的肩膀说,小伙子,先忙别的去吧。
崔永元并未灰心,借着央视制播分离的改革机会,自己筹钱开始做这个项目
。
在2010年5月15日崔永元的新片《我的抗战》的看片会上,崔永元透露,七
八年来,他和他的团队筹到1.2亿元,采访了3500个人,收集的口述历史的影像
超过了200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300万张。而最大的困惑是,对抗战
历史最感兴趣的,竟然是我们当年的对手日本人。
在这次看片会上,崔永元直言,其目的就是“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
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高考时历史成绩高达96分的崔永元说,尽管上学时学
到不少的假历史,但他都“倒背如流”,后来开始看书、听别人讲、上网,知道
哪些是假的,激起了他浓厚的兴趣,“我一定要知道真的是什么样。”
参加这次看片会的导演康洪雷也坦言,他和编剧兰晓龙在采访完中国远征军
老兵回到酒店后相对号啕:之后我们在想,哭什么呢?是哭这些老兵壮丽的往事
和寂寥的今天?还是哭什么?后来发现,我们哭我们自己的无知,自己的可怜。
我们快五十岁了,居然连中国抗战历史上这么大块波澜壮阔的史实都丝毫不知,
不可悲吗?
正因为此,才有了后来反响巨大的电视连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而拍这
部片子,“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真相或许永远也难以企及,但一步步地逼进
真相,就是成功。
戈叔亚开始专门研究二战史也是因为“受了刺激”。那是在1983年,他因为
生意上的事路过腾冲,当他无意中看到国殇墓园门口的石碑时大为震惊,大学历
史系毕业、且在大学时选修二战史的他竟然对这段历史毫不知情。从那以后,戈
叔亚放下生意上的事,开始奔走于滇西的村村寨寨,逢人就打听那段历史。
史料严重缺乏,他不得不从收集老兵的口述开始。
采访这段历史的记录者让人上瘾。我们不能再等了
对此,崔永元曾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比喻:于丹的《论语心得》特别火,为什
么火?不就是因为没有孔子的采访吗?如果陈晓卿的《见证·影像志》一天一集
孔子的采访,谁还听论语心得啊。
真的不能再等了!如果在1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我就发起组织流落缅甸
的中国远征军回国寻亲团,那该是一支多么壮观、多么抖擞的队伍啊!
李锡全成功回家探亲之后,我开始谋划一个更大的计划:尽最大努力去采访
更多的流落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然后为他们找到家,再接他们回国寻亲。
虽然比起李锡全一个人回家来说,这个活动难度更大。我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许多参与活动的志愿者都感慨,不知道第二天会面对什么,不知道老兵的回
家之旅会不会因为一个意外而戛然而止,我们每一天都在忐忑、失望、狂喜中度
过。
“走啊,我带你们回家”,这是《我的团长我的团》里的一句台词,有点神
经质的伪团长龙文章,就是利用这句话,给了那群残破不堪的溃兵们一个希望,
让这些溃不成军的败兵走在了一起。
“走啊,我带你们回家。”从再次前往缅甸的时候开始,我就不停地默念着
这句话。
7.颠沛中生,寂寥中死,是什么让命运如此多舛
我曾经在许多公开的场合向大家讲过仰光的老兵陈华的故事,听的人,大多
都会热泪盈眶。其实每一个流落在缅甸的老兵的故事,都可以拍成一部大片。一
个个体的命运,面对数以万计伤亡的战争,面对半个多世纪的党派恩怨,面对寄
人篱下的异域生活,真的微如狂风中的一粒尘埃。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寻找陈华的那段场景。那是在2009年3月11日的午后,
仰光的华侨陈自廷开着一辆右舵的丰田车,带着我穿行在仰光的华人区。街道狭
窄,头顶是交织凌乱的电线,不时会有几只鸽子飞过,路两旁的楼房已经破旧不
堪,从阳台的状况可以发现,一些房屋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陈自廷告诉我,
这里居住的华人,很多是1949年前后从大陆逃亡而来的,而今,他们中的第二代
、第三代已经有好多通过各种方式去了台湾或者美国或者泰国,当年那些趴在父
母背上或者坐在父亲肩头的挑担上翻越国境逃难的孩子,如今也是花甲老人。在
子女为了更好的生活再一次去了异域之后,年迈的他们也只能在孤寂中度过余生
。
陈自廷说,这里的很多老人,都是一个人居住,有好几个老人都是在家中死
去多日后才被邻居或亲人发现的。
颠沛中生,寂寥中死,是什么让命运如此多舛?
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华人聚居区里找到了陈华。从热带的阳光下走进一个阴
暗的小门洞,然后是一段又窄又陡的木制楼梯,伴随着咚咚作响的声音上到二楼
,一位戴着眼镜、面容清瘦的老人正坐在沙发上一脸平静地看着我。如果不是头
顶缓慢转动着的三叶吊扇发出的单调的嘎吱声,真的会感觉时间已经停滞。我似
乎觉得,这位老人已经用这种姿势等了我好多年。
1920年出生的陈华祖籍湖北汉口,父亲在其两岁时就因病辞世,坚强的母亲
将他们兄妹七个拉扯大,并尽最大的努力让他们上学。抗战爆发后,在南京上学
的陈华遂入伍成为部队的一名汽车驾驶员,并在松沪会战时,担任弹药粮食补给
工作。不日南京沦陷,陈华调往重庆,担任成渝公路军运工作,后到贵州辎重兵
学校受训,之后调往云南,在联勤总部四十三分区司令部任上尉参谋。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陈华等多人化装后
离开昆明,后经畹町进入缅甸九谷,在逃亡过程中被关进缅方的密铁拉难民营。
在逃离昆明之前,陈华将妻子黄惠和一儿一女送往四川内江妻子的娘家,那
时,妻子正有身孕。他告诉妻子,等时局安稳之后,他们再全家团聚。
陈华在难民营里一直被关押了三年时间。最初,他和妻子曾有书信来往,妻
子在来信中鼓励他,并介绍他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全
家团圆的希望日渐成为泡影。最后,陈华不得不告诉妻子,别等他了,改嫁吧,
他唯一的要求是改嫁之后,能否念及夫妻情分,亲生子女都保留陈姓。
陈华被难民营释放之后,辗转前往仰光定居,并娶妻生子,其中两个女儿分
别叫陈忆南和陈忆惠。南指云南,惠取自妻子的名字。
星移斗转,40多年后的1990年3月18日,这个让陈华永远也无法忘记的日子
,一位缅甸的克钦族女人突然找到陈华的家里,交给他一封信。莫名其妙的陈华
打开信,开头这样写着:父亲大人,离别四十多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与父亲
联系,还请父亲大人原谅……
刚满古稀之年的陈华失声痛哭。
写信的人是当年还在襁褓中的大儿子陈传志。陈华了解到,这么多年来,儿
子一直在打听他的下落。有一天,前往云南瑞丽做生意的陈传志碰到了一位缅甸
的女生意人,就将此信交给了她,托付她去寻找父亲。这位缅甸商人多方打听,
终于在仰光的云南青年会打听到了陈华的消息。
大约一个月后,陈华终于在云南瑞丽见到了离别40多载的儿子,包括当年离
家时还在娘肚子里的小儿子陈传毅。随后陈华又抵达四川内江,见到了大女儿以
及妻子黄惠。妻子已嫁他人,并且育有三个孩子,两人只能相视而哭。
8.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一定要去野人山祭奠那些在逃亡中被遗弃的英雄
此次前往缅甸采访老兵之前,我曾接到一个寻亲的电话,来自山东章丘。来
电话的人说,他有一个伯父当年参加了中国远征军,直到2005年5月,他们收到
了伯父从缅甸曼德勒写回来的信,还寄回来照片,他们也照地址回信过去,但再
也没有回音。他的伯父名叫刘权,是他父亲的亲哥哥,他的父亲自从得知哥哥在
缅甸的消息后,一直期盼此生再能见上哥哥一面,整日看着哥哥的照片,以泪洗
面。
在仰光采访完老兵陈华,我立即飞赴曼德勒。曼德勒多省籍同乡会副秘书长
王荣森告诉我,刘权在半年前刚刚去世。提到2005年5月他向山东的家里写的那
封信,王荣森说,那封信还是他帮着写的,因为那年9月刘权刚好有一个机会到北
京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座谈会,想借此顺道回山东老家探亲,但没想到,直到他
从北京回到缅甸后,他才收到了家乡的回信。
在王荣森的带领下,我去了刘权家里,是一幢二层小楼,家里只有刘权的孙
子在,一位30岁左右的小伙子,不会说汉语。王荣森说,刘权曾向他多次表露过
想回山东老家的愿望,但得不到子女的支持。在晚年,刘权过得很是孤单,因为
曾经受过牵连,他的子女一直不愿意他和其他的老兵来往,甚至在刘权过世之后
,一些老兵前去吊唁,也被拒绝。
刘权赴北京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座谈会,是因为中国驻缅甸曼德勒总领馆的
努力。2002年,总领馆曾组织9位老兵到云南旅游;2004年,又有几位老兵参加
了在腾冲举办的中缅印战区滇西战役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刘权和杨伯方两
位老兵代表,参加了在北京的抗战胜利60周年座谈会。
由旅游始,到学术研讨,再到中国的首都参加官方的座谈会,历史就这么一
步步地走上前台。
正是因为大使馆和总领馆的努力,流落缅甸的大部分老兵都领到了2005年由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
章。而在国内,很少有国民党的老兵能领到这个纪念章。
和刘权一起去北京的老兵杨伯方,在老兵中有着很高的威信,也是我一直想
要拜见的一位老兵。《云南信息报》副总编辑王雷在2005年曾采访过杨伯方。杨
伯方告诉他,“我们缅甸老兵们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再戴上军功勋章,在欢呼声
中,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心高气盛的杨伯方最终未能等到这一天。在2009年1月2日,与世长辞。
后来我在凤凰卫视编导苏园2001年拍摄的一段视频上看到过杨伯方,满头银
发,精神矍铄。印象最深的是他亲历的一件事情。在第一次入缅作战遭受重挫后
,在逃亡过程中,杨伯方所在的运输连里的一位战士被汽车轧断了右腿,其他战
士就抬着他走,但天太热,这位战士的伤口已经化脓,而更让人为难的是,他们
要翻一座陡峭的山,一个人走就费劲,抬着这位伤员走基本不可能,而丢下他,
他肯定是死,不是饿死,就是被老虎吃掉。就在大家不知所措之际,从后面赶上
来的一位指导员悄悄告诉杨伯方,别犹豫了,打死他吧。在万般无奈之下,一位
战士拿出冲锋枪,压上一颗子弹,趁着这位伤员不注意,对着他的后脑勺开了一
枪。之后,大家挖了一个土洞将他掩埋。在后来的行军中,大家都很压抑,没有
人说话。这位指导员说,“你们不要埋怨我,他死了,还有人埋他,而我们呢?
我们死了,谁来埋我们?”
杨伯方讲述的这件事情发生在野人山。
野人山位于缅甸北部,喜马拉雅山之南。那是2002年的一天,一位缅甸的军
官在一次追捕几名地方武装组织的叛军时,来到了野人山,在原始森林里走了三
天三夜,之后偶然发现一个山洞,进去一看,里面遍地骷髅,横七竖八。在骷髅
中间,散落着锈迹斑斑的枪、徽章以及发报机等。这位缅甸军官知道,那是中国
兵。
1943年10月,驻印远征军反攻缅甸时,曾在野人山的胡康河谷和日军展开激
战。参加作战的新38师的战士们,在这里见到了许多当年败退时经过此地的第5
军将士,但只是一堆围着枪架而坐的白骨。不用多说一句话,这些增补的新兵的
亲眼所见,已足以激起他们内心的愤慨和战斗的豪情。
我一直在想,等有一天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一定要去野人山,去祭奠那些在
逃亡中被遗弃的英雄。
9.人生为二,一是离开学校拿起枪打 日本,二是放下枪在异域教授中文
如果不是战争,张富鳞觉得,自己在国内肯定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专家或者教
授了。
1941年,正在山东第一师范读书的张富鳞,和全校老师以及其他男同学一起
,弃笔从戎,走上抗日救国之路。半个多世纪之后再回想那些日子,张富鳞感觉
很是幼稚,“那时我们把行李全部放在了学校统一保管,说等打完仗之后再回来
取行李,谁还能知道,再也没能回去。”
张富鳞参加的是隶属于宋子文的中央税警团。1941年12月,税警团改编为新
38师,孙立人任少将师长,张富鳞是师部通讯兵。这支私人部队,经过两年的训
练之后,成为国民革命军最为精锐的部队之一。1942年,张富鳞随着部队入缅,
参加了仁安羌大捷。此次战役,新38师的113团,与7倍于我的敌军激战两昼夜,
最终完成解救被困的7000余名英军的任务。
抗战胜利后,张富鳞留在了缅甸,于1950年和缅甸傣族的一位姑娘成婚,并
在随后进入一家华文学校教授物理和化学。华文学校被收归国有后,张富鳞又到
随后兴起的孔教学校教授语文,直到80岁退休,前后共教书40年,目前每月有
33000元缅币(约200元人民币)的退休金。张富鳞有5个孩子,都是大学毕业。
“你说,在中国,像我这样,抗战时就上过师范,教了40年书,还穷酸成这
样?”张富鳞说,自己的历史分为两部分,一是离开学校拿起枪打日本,二是放
下枪拿起粉笔在异域教授中文。
“我对得起祖国。”张富鳞说,“美国总统肯尼迪曾经说过,不要问你们的
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我为国家做了这两件事
,我觉得,我对得起祖国。”
接受采访时,张富鳞特意穿上一件白色的别着两枚纪念章的上衣。两枚纪念
章,一枚是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
发;另一枚则是广西一个关爱老兵的民间组织颁发。
前一枚纪念章直径为50毫米,正面铸有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人民大团
结的5颗五角星、象征人类和平的鸽子和橄榄枝,还有革命圣地延安的宝塔山,以
及军民合力抗战的战斗场面。这枚纪念章的介绍文字上写着,“本纪念章是由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题写章名,颁发给参加过抗
日战争的老同志。”
远在异域的老兵们能得到这枚纪念章,其中还有很多的故事。
2002年9月15日,在中国驻曼德勒总领馆的组织下,9名老兵组团重返云南,
并前往腾冲的国殇墓园为战友敬献花圈。这次回国访问,是以参观旅游的名义,
而且访问团全称叫缅甸华人华侨访问团,并没有出现中国远征军的字样,且回国
的老兵都被组织方叮嘱,不得接受媒体的采访,一切低调行事。
当时参与组织此次活动的王荣森称,他开始找老兵说此事时,好多老兵都不
愿意回去,“虽然那是他的祖国,但毕竟是共产党执政的地方。”经过多次做工
作,终于有11位老兵答应回国访问,“就在临出发前,又有两位老兵因为孩子的
反对未能成行。”
缅甸华人华侨访问团的成功访问,打消了众多远征军心中的疑虑,一些老兵
为此向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提出,花那么多钱回国访问,还不如花几块钱人民
币给他们发一张证明,“只要说我们打过日本鬼子,为国家作过贡献就行。”
随后,几位老兵以缅甸现生存之抗日远征军的名义向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
递交请愿书:“恳乞祖国政府有关方面,给予追认远征军的史实和功绩,有所表
现(不过一纸褒奖,作为抗日纪念而已),以慰炎黄儿女血洒异域的壮烈事实…
…”
老兵们的请愿得到了总领馆的高度重视。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领事张建兴
说,向中国远征军老兵发放纪念章一事,他们早就有想法,到2005年抗战胜利6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他们向中央提出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
每一个人都想被承认,何况那些为了国家流过血丢过命的人。
在曼德勒采访张富鳞的时候,他也多次提到“承认”。说到激动处,张富鳞
总会反问我,“你说,中央电视台为什么不来采访我?为什么?”十多年前,曾
有一位记者采访过张富鳞,但最后稿件并没有发表,“那个记者说时间不对,你
说,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我们都死光了吗?”
然后,张富鳞扳着指头给我数已经去世的老兵,“杨伯方死了,刘权死了,
曾伯琴死了,边一帆死了,陈达夫也死了……”
曾做过孙立人通讯兵的张富鳞说,师部里好多重要的材料他都亲眼看到过,
“有的东西,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道,现在不赶快把这些东西收集记录下来
,等到有一天,你们意识到这段历史的重要了,却没有人能告诉你真实的历史了
,你们听到的都只是故事,不是历史了……”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