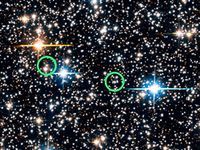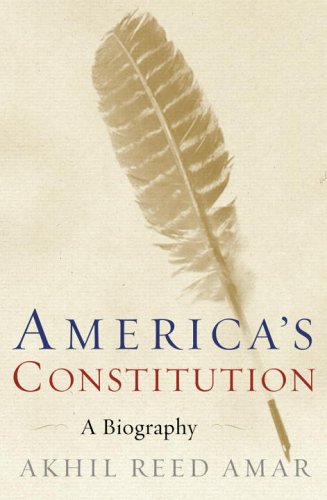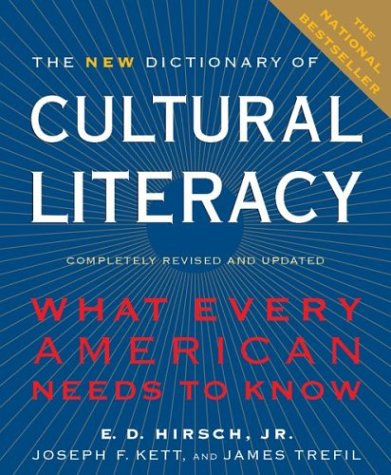高鸿钧:《黑客帝国》的隐喻:秩序、法律与自由
《清华法治论衡》第12辑“社会理论之法前言”卷首语
在“社会理论之法”的论题中提及《黑客帝国》,犹如在麦当娜的话题中扯上麦当劳,似乎离题太远。然而,当我们注意到以下线索,就会觉得这种联想也许并非牵强附会。在那部影片中,一个黑客去同尼奥私下交易,尼奥从一本掏空的书中拿出一张非法软件,《拟像与仿真》的书名随之闪现。这个特写镜头暗示影片与作品的潜在联系,也传达了导演对该书作者的敬意。该书作者是是当代社会理论大师鲍德里亚,导演卓斯基兄弟是他的书迷,影片立意、话语和意象无不闪烁着鲍式的思想、洞识与灵感。另一个线索是,德国的托依布纳是卢曼社会系统论和法律系统论的得力传人,他在《匿名的魔阵:跨国活动中“私人”对人权的侵犯》一文中,所使用的“魔阵”一词是Matrix的中文译名,而“黑客帝国”恰是Matrix另一种中文译名,两者都是对现代社会的隐喻。
一
Matrix是什么?它是母体,是魔阵,是系统,是控制。它是我们最大的敌人,置身其中,四处一望,我们可以见到官员、商人、教师、律师、木匠以及其他芸芸众生。Matrix无处不在:当我们置身办公室、课堂、会场、股市、网络、厕所以及睡梦中,它都如影随形,跟踪着我们,控制着我们。正是这个Matrix蒙骗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真相,麻醉了我们的神经,使我们觉察不到虚假。它禁锢了我们的大脑,使我们失去了反思意识;束缚了我们的手脚,使我们丧失了反抗能力。我们处在战时,却误以为和平;成为了奴隶,却误以为自由;拥抱愚昧,却误以为追求真理。于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在这个系统里,我们是一段被编码的程序,代码决定了我们的功能,架构决定了我们的选择范围。在那里,我们选择程序和被程序所选择,我们甚至选择了超出自己理解能力的选择,而对于选择的真正考验就是再次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人们或者不能预测自己的选择结果,或者对他人的选择结果不能预测。我们有时知道应该怎样选择,却不能那样选择,有时虽然知道能够那样选择,但又不知道怎样选择。这是一个选择的世界,没有管辖、没有控制和没有界限的世界,一个什么都可能发生的世界,选择就是一切。关键不在于选择什么,而在于使人们感到是自己在选择;关键不在于事实是什么,而在于使人们相信事实是什么。
在这个系统中,没有价值而只有程序,正如景观社会没有本真而只有模拟。程序驱动程序,程序复制程序,程序打劫程序,程序删除程序,程序就是一切,正如模拟复制模拟,模拟盗取模拟,模拟覆盖模拟,模拟就是一切。程序与模拟产生诱惑,诱惑源于诱因,诱因产生意义。没有意义就没有我们的存在,意义创造我们,链接我们,操纵我们,指引我们,驱动我们;意义规定着约束我们的意义,决定着我们所追求的意义。意义即游戏,游戏而陶醉,陶醉而眩晕。
意义自有原因,于是我们去理解各种原因,是原因区别了我们和你们、你们和他们;区别了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区别了过去与未来,现实与理想。原因是力量的源泉,没有它就没有力量。然而,原因很快就不再重要,重要的只剩下感觉。感觉是对结果的品味,品味来自刺激,刺激源于诱因,于是我们都是刺激的俘虏和诱因的猎物。凡事都有定期,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播种有时,收获有时。有时天行有常,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时天秩失序,种下龙种,收获跳蚤,孵下凤蛋,跳出秃鹫。只要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应该发生的事情,而应该发生的事情未必将会发生。社会是另一种自然,人性是另一种动物性,法律是另一种政治,代码是另一种法律。
Matrix是一个主机控制下的系统网络,人们一旦与之链接,就不愿断开,许多人已然适应而且上瘾,离不开这个系统,转而会捍卫它。于是,我们宁愿选择红药丸,生活在虚假的感觉奇境中,而不愿选择蓝药丸,寻找荒漠的真实世界。在那个奇妙的世界,我们都可能既是受监视者又是特工,既是受虐者又是施虐者,既是人质又是恐怖分子,既是自己又是自己的敌人。
上述语言和情景不是《黑客帝国》写照吗?那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一个机器控制的系统。然而,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韦伯的“铁笼”,福柯的“规训社会”,卢曼和托依布纳的“自创生系统”。在边沁那里,“全景敞视监狱”是控制囚犯的完美设施;在韦伯那里,自由的生命个体在算计和博弈中,最终却落入了形式理性的牢笼;在福柯那里,宣称解放的人类,最终却把社会打造成规训无所不在的牢狱;在卢曼和托依布纳那里,现代社会和法律都分化成铁板一块的系统魔阵。系统自我建构、自我描述、自我调节、自我维持、自我操作、自我创生;它是沟通的建造物,是代码区分的二元世界。于是就有了君子与小人、信徒与异端、人民与敌人、以及合法与非法之别,于是控制就变得简单,规制就来得方便。系统虽然无所不在,却又无影无形吗;虽然无所不知,却可以对外界充耳不闻;虽然无所不能,却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系统是个匿名的魔阵,人们无从反抗;系统的“滤霸”不断升级,随时过滤杂音,删除乱码。
二
如果说Matrix就是社会的缩影,那么,它不是一个扭曲和虚假的社会吗?然而,正常和真实的社会又在哪里?柏拉图说,它在理想国里,现实是一个扭曲的洞穴。然而洞穴中的众生已经过惯洞穴中的生活,真实世界的阳光特别刺眼,于是人们宁愿生活在洞穴中,在黑暗中捕捉真实的虚影。实际上,在哲学王领导的真实世界里,人类并没有真正的平等和真实的自由。在那个理想国里,国王还是国王,士兵还是士兵,奴隶还是奴隶,所不同者只是国王用哲学统治,士兵具有了“卫国者”的光荣称号,奴隶换成了另一批“会说话的工具”。由此看来,那个真实的理想国,不过是另一个虚拟的洞穴,变化在于精神控制代替了身体枷锁。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如果说传统的宗教救赎带来的是精神奴役,那么现代的解放追求打造的则是规训铁笼。绝对精神只有在自我献祭中才灵光偶现,永久和平凭靠的是核威胁的恐怖平衡,无产者在世界边缘分化成碎片,资产阶级在全球中心结成了铁盟。坚船利炮换成了跨国公司,传教士换成了大律师,八国联军换成了G8峰会,《南京条约》换成了《华盛顿共识》,自然法变成了人类之法。昔时丛林游击队长变成了今日铁政治腕,当年工会领袖变成了当下法团巨头,自由主义者把自由变成了意识形态教条,民主主义者却以专政方式推行民主。于是历史充满了变数和吊诡:政治是战争的继续,经济是军事的替代,法律是政治的变种,文化是时尚的别名,和谐是冲突的间歇,梦幻是现实的投影。从红场到黑海,到处都矗立着权力的凯旋门;从多瑙河到莫愁湖,处处都闪烁着货币的金字塔。等式似乎永远平衡,变化的只是因数,余数被省略了。
面对这个充满魔力的Matrix所施展的“吸星大法”,老左翼在历史发展的“否定的辨证法”中陷入悖论;新工党则改弦易辙,匆忙中把“人类动物园”改建成“丛林迪斯尼”;后现代主义在精神呜咽中叙说着对文明的不满,并在审美迷狂中实现着自我超越;新保守主义则根据旧版社会达尔文主义,热泪盈眶地宣布新自由主义是“历史的终结”;而原教旨主义则在极化地方性知识的精神亢奋中,从恐怖战略中发现了行动的力量。于是,热血青年从街头广场退入购物中心,产业工人急于把蓝领换成白领,莘莘学子则迫不及待地加入房奴、车奴和卡奴的虚拟矩阵。政治领袖在继续忽悠民众的同时,想方设法完成知识符号的现实超度,因为他们深知,知识就是权力,技术官僚就是系统控制的工程师,没有知识的权力,技术官僚就缺乏控制的力量;没有权力的知识,系统工程师的控制就无从谈起。
幸运的是,信息技术为人们建构了一个虚拟世界。人们在那里享受空虚的充实,而不再忍受充实的空虚;可以把陌生人变成老熟人,把老熟人变成陌生生人;把妻子变成情人,把老板变成老公。真实世界是荒漠的废墟,单调而乏味,压抑而拘束,而虚幻世界则是奇妙的仙境,丰富而有趣,轻松而自由,因而《黑客帝国》中一些选择了蓝药丸的战士十分后悔,想要重返虚拟世界,想要品味鲜美的牛排,不愿再强咽无味的稀粥。为此,他们不惜背叛队友和进行疯狂报复。
科学探索实在,却筑造出虚拟世界;理性祛除巫魅,却使世界陷入疯狂。对于这种吊诡,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想不清楚,说不明白。疑问萦绕着我们的头脑,困扰着我们的心灵。我们对于现世感到无奈,就寄望来世天堂;对现实不满,就逃向虚拟世界。天国之城虽然没有征服尘世之城,虚拟世界却覆盖了现实社会。
在网络编织的虚拟世界,世界数字化,生活虚拟化,生命游戏化,灾难戏剧化;在那里,红色歌曲,黑色幽默,绿色革命,白色恐怖,桃色事件,黄色笑话……应有尽有。在那个“网络共和国”中,人们不再是“贾雨村” 或“甄士隐”,而是“门修斯”或“常凯申”;在那个“信息乌托邦”中,人们不再“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可以思想裸露,精神裸奔,身体裸聊,可以建社区、偷白菜,包二奶……一言以蔽之,那里可以言现实想言而不敢言,为现实想为而不敢为,而不再限于“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作为未来的代言人,我代表未来,要求过去的你们别管我们。在我们这里,你们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巴洛的《网络独立宣言》对于网络世界的自由似乎信心十足。
然而,这一理想不久就灰飞烟灭。虚拟社会天生也不自由,规制它的是架构和代码:架构就是约束,代码就是法律。代码是一种变相的规制,正如凝视是一种无声的语言。虚拟社会天生也不民主,统治它的是编程者、黑客和监控者,编程者设下程序“枷锁”,扣下代码“暗杠”,黑客的“特洛伊木马”游荡在我们信息隐私的王国中,随时可以攻陷我们的“城堡”,而无所不在的电子蠕虫就潜伏在我们的网络头脑中,随意透视我们的每根神经。虚拟世界之于现实社会,颇似马克思针对路德教所言: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枷锁”。在虚拟世界,我们的“另一个自我”和“第二人生”再次不幸地陷入了规训之网,与真实世界不同的是,那里的立法者主要是隐形程序师而不是在场政府,执法者主要是技术诀窍而不是政治权力,法律规则主要是代码不是法典,司法者不再是法院法官而主要是……
虚拟世界造成了信息偏食和群体极化,带来了网络贩毒和在线卖淫,导致了违法与犯罪的隐蔽化、跨国化和全球化,而这一切都对现实社会构成了侵害。于是,现实的法律对网络的架构和代码进行规制。由此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相互联通。更准确说,虚拟世界是现实社会的翻版,现实社会是虚拟社会的投影,扭曲社会是正常社会的镜像,正常社会是扭曲社会的别称,正如数字不过是自我的心理投影,真实乃是大脑中的刺激信号。技术控制比权力统治更有效,代码规制比法律调控更直接,私人管制比政府治理更便捷。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虚拟世界中自以为自由的网民,也许比现实社会之人更是奴隶。
三
如果说“锡安”是人类的缩影,它被自己的制造物逼入绝境之后,生存迫令自然就是“拯救锡安”。“锡安”隐喻上帝子民之城,暗指基督教圣地,是西方世界的缩影。于是就有了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自我是西方,是正义的真实社会;他者是非西方,是邪恶的虚拟世界;正义与真实的化身是尼奥,邪恶与虚拟的符码是史密斯,于是一场进攻与防卫、恐怖与反恐怖以及生存与灭亡的大决战不可避免。虚拟世界的机器人强大无比,不然,便不足以表达人类恐惧之深,不足以彰显人类危机之重,更不足以体现人类拯救之迫。尼奥隐喻耶稣,一位黑客出身的“克里斯玛”,他要破解母体自我繁殖的密码,改变等式平衡。
然而,尼奥毕竟是凡人,要对拯救使命有信心,还需要一点外力。这就是“先知”预言的力量。预言者是希腊oracle(神谕者)的现代版。女性身份增加了预言的神秘,据说女人比男人更易着魅和更能通灵。她的黑白混色皮肤或许暗喻种族平等,但与歌星杰克逊无关,因为他曾极力把身体漂白,且同具男女性征。当然这更不是兆示奥巴马当选,因为他即便皮肤黝黑,当选后是否会把观念漂白,尚不可知。预言的奥妙在于模糊,就如生活的真谛在于糊涂,生命的真谛在于操心。与刘姥姥三进大观园不同,预言者多次出场,但她所透露的“天机”不过三条洞见:认识自己,改变的不是物象而是意念,预言具有自我实现的效应。这三条看似是平常道理,但内涵都是吊诡或悖论。自己是自我观察的盲点,认识自己是个悖论;事物的本质是观念的产物,我们对自己的观念无法同时进行二阶观察,这也是悖论;乐观的预言未必兑现,悲观的预言却往往应验,这里充满着吊诡。先知的言谈举止和周围环境都暗示她来自生活世界。这自然让我们联想到,哈贝马斯寄望生活世界,希望那里的日常语言所承载的交往理性能够生成合法之法,从而降服政治系统的权力之妖和经济系统的金钱之魔。就此而言,哈贝马斯是一位预言者。
昂格尔是另一位预言者,他宣称自由主义的形式法业已解体,取而代之的法范式或许是源自生活世界的习惯法。这种视角与埃利希的“活法”暗合。这两位预言者的预言并没有很快应验,欧陆的法典“死法”早已把埃利希的生活“活法”吞没,而美国的自由主义形式法并未解体,解体的却是预言者所创建的批判法学流派。不过,在法律全球化过程,他们的预言有些歪打正着。新商人法以商人私约的形式成为了“活法”,逃避了主权的规制,托依布纳说这是埃利希“活法”预言的兑现。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来自经济系统的“活法”却成为规避劳保和环保的“腐败之法”。生活世界也许是个未经反思的习俗“荆丛”或巫魅之乡,那里流行过美国南部的《黑奴法典》,“焚寡殉葬”的印度乡之俗,或许会联想到犹太人的割肉还债之约。抛掉了锁链上的假花,并不是为了戴上没有任何花朵的锁链;否定了敷粉的发辫,并不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辫打交道,马克思的名言可以作为一种警示。真正自由的活法是公民自我立法,只有在交往理性滋润的生活世界才能够生成这种活法。这种活法也许存在自主公民的观念中和公民自主的行动中,存在于基本人权与人民主权的互动中。
尼奥不是史密斯的对手,因为史密斯是尼奥的负相,正如人类不是机器世界的对手,因为机器世界是人类社会的翻版。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尼奥一定要牺牲,否则就缺乏悲壮;尼奥也一定要复活,不然就没有希望。于是,那个古老的神话——爱情,便成为了牺牲与复活的媒介,只是把传统的叙事顺序颠倒了一下:不再是英雄救美人,而是美人救英雄。性爱只能激活个体的灵魂,救世主的复活却能带动集体精神,只有“克里斯玛”与芸芸大众的相互诱惑和一道眩晕,才能成就拯救世界的伟业和壮举。这又落入了韦伯政治方案的窠臼。
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尼奥不过是一段超级程序,而“先知”也不过如此,他们的合谋与“锡安”大众的合力,也无法应对虚拟世界的进攻,因为系统的代码早已设定,程序按其功能迫令,是其所是,成其所成,毁其所毁,灭其所灭。更何况机器人比人类更少怯懦和私心——设计时把这些基因缺陷剥除了。这就需要尼奥返回源代码,会见程序设计师,通过改变源代码改变等式平衡,改变系统的运行逻辑。马克思、尼采、福柯和哈贝马斯尽管路径不同,都认为现代性问题主要出在源代码上,都想设法改变现代社会的源代码。
四
系统一旦运行起来,就会形成自我复制和自我维持的逻辑习性,就会诱导人们适应和上瘾,改变源代码必然引起程序混乱和功能失调。程序设计师只有在感到“史密斯”会失控时,才会同意尼奥的建议。改变者与维护者一场生死搏斗在所难免,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尼奥只有先染毒才能消毒,而成功意味着与“史密斯”同归于尽。通过消灭自己来消灭敌人,一如系统通过改变自己而改变环境,这本是就是一种悖论性博弈。至此,影片所演绎的古老故事,即正义与邪恶之战,似乎落下帷幕,关于耶稣牺牲自我拯救世人的新版隐喻,也已了然。剩下的一个问题则是,既然机器世界是人类社会的复制品,虚拟世界是真实社会的投影,源代码的彻底改变,是否要以“锡安”的毁灭为代价?
对于现实社会的Matrix,人们即便能够发现源代码,返回源代码并根本改变它也几无可能。权力和金钱两个代码,控制人类社会为时已久,权戒与钱戒之难,难于毒戒与赌戒,也难于网戒与色戒,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我们基因的另一半,正如撒旦是天使的另一半,男人是女人的另一半,股市是赌场的另一半。这就不难理解,任何推翻过去压迫的尝试,都没有带来解放的现实,任何翻转现实统治的超越,都打造了另一种未来的统治现实。如果说传统法律承载的是等级特权,身份奴役,压抑人格、机械团结和施舍正义,那么,现代法律所内含的则是自我分层的平等,自我放逐的自由,自我分裂的人格,自我分化的团体以及自我颠覆的正义。前者是弱肉强食的历史墓志铭,后者是自我解构的现代讽刺画。解决问题的方案有时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就如医治病人的疗方常常会带来更多的病症。完美世界如同完人,只存在于幻想之中,正确的答案所以一直在回避我们,也许是因为我们过于满足现实或追求完美,因而丧失了去弊和纠错的机缘。
诅咒过去与讥讽现实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正如期待来世与盼望天国无益于苦难的解脱。树上不言树下事,十分世界在眼前,禅宗的“当下即是”显得更为脚踏实地。无论是生命政治的倡导还是交往理性的吁求,无论是对“活法”的善意期待还是“宪法爱国主义”的良苦用心,虽然对于改进社会现实都不无启示,但似乎都无法改变现代社会的“源代码”及其运行逻辑。我们以为,真正的契机和希望也许既不在于整体建构或彻底颠覆,也不在于置换源代码或理性重构,而在于社会危机的压力和对灾难的反思,因为正常时没有人会思考为什么会正常,更不要说改变了;在于有识之士的现实批判与公民大众的权利吁求,因为既得利益者大都满足并维护现状。当奴役成为一种常态,人们就把奴役当作自由,当羁縻成为一种秩序,人们就把就羁縻称为解放。
对于社会的反思来说,一万句苦口婆心的劝谏,不如一个灾难的教训更有效;对于人类和平而言,一千个世界主义的口号不如一次残酷的战争更有效;对于系统的调整来说,一百种环境刺激不如一次重大危机压力更有效;对于民主和自由来说,数十部宪法不如一个个自主的公民更有效。故而,马克思从阶级压迫中预见了解放的动力,康德从战争的残酷中看到了永久和平的曙光,福柯从权力的规训中洞悉了个体伦理完善的重要性,哈贝马斯从生活世界自主公民的呐喊中察觉了现代性的希望。为此,我们需要的是愚公移山的行动,是普罗米修斯的勇气,弗弗西斯的耐力,夸父追日的悲壮,精卫填海的坚持。
有些事情永远不变,有些事情应该改变。必须坚守永远不变的事情,必须改变应该改变的事情。于社会是如此,政治是如此,法律是如此,于个人也是如此。
己丑年秋
高鸿钧于清华园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